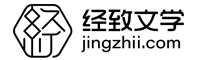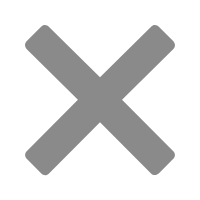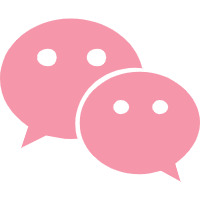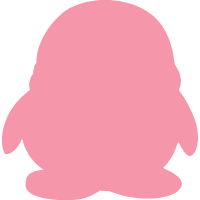-
雪落云归处,爱恨已成空
本书由经致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1章
援藏支教的第八年,丈夫带着白月光来雪山求婚。
“不过是演场戏逗小姑娘开心,又不是真的领证,你计较什么?”
他骂我不够大度,求婚成功后又逼着我给他们做向导,带他们爬雪山,直到遇到雪崩。
生死一线间,他当即牵起白月光的手逃离,看着我滚下山坡:
“当年若不是因为你在雪山上无意中救了奶奶挟恩图报,我和昭昭也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如今她也怀了我的孩子,天意如此,你就当是把这个位置还给她吧!”
我心如死灰,忍痛坚持,直到被搜救人员找到。
然后,我叫住了那个守在我身边一整夜,却在我醒来时就想仓皇逃离的男人:
“梁先生,三年前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
1
直到梁牧离开时,我还觉得有些恍惚。
三年前,他在藏南对我一见钟情,向我表白,却得知我已经结婚。
他向我保证不会越界,但还是却追在我身后整整三年,每年都会来这里陪伴我,默默守护,只当我的“朋友”。
而我却也没想到,三年后的今天,我会选择结束那段坚守了八年的感情,答应他的追求。
“我喜欢你,我说过,我永远都是等你的那个人。”
我看着他欣喜若狂的眼睛,知道他是百忙中飞到这里,所以提出让他先回去,也给我留一些处理事情的时间。
而他前脚刚走,我就接到了程兆川的电话:
“听说你没事,现在在哪?昭昭很担心你……”
“程兆川。”我握紧了手机:
“我们离婚吧。”
对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过了片刻,程兆川恼怒的声音才响起:
“就因为方才雪崩我没先救你,你就要任性到这个地步?”
任性?
我嗤笑一声,想起雪崩时他对我说的话。
他怨我挟恩图报,怨我抢了许昭意的位置,盼着我死在那场雪崩里。
可当年,明明是他紧追不放,说绝对不是为了报答我救下他奶奶的恩情,只是被我的善良打动,求着我答应他,嫁给他。
既然他已将前事忘却,颠倒黑白,那我也不必留恋了。
“别开玩笑了,你没什么事就回民宿这里,昭昭受到惊吓吐得吃不下饭,你对这里的气候饮食比较了解,赶紧回来做些好入口的给她”
他侃侃而谈,仿佛方才我经历的生死一线根本不值一提。
而我看着远处巍峨壮丽的雪山,打断了他:
“我说了,我们离婚。”
“我也不是你们的保姆。”
然后我飞快地挂断电话,躺在病床上,心如死灰。
这场雪崩让我的左手手臂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还伴随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治疗。
当然,若不是我求生经验丰富,我可能真的会死在大雪中。
“老师!”病房门被推开,几个孩子跑进来,担心地围在我身边。
我望着他们清澈的眼睛,笑着安慰他们没事,心下熨帖。
这些孩子,永远是我的牵挂,也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
“谢云卿,你到底在装什么!”病房门被推开,程兆川沉着脸大步走进来,一把拉起我骨折的左手。
我吃痛闷哼了一声,他诧异地看着我打着石膏的左臂,手一松,一个一直待在我身旁还未离开的小男孩就冲过去拦在他身前,道:
“不许欺负老师!”
而跟在他身后的许昭意仿佛受到天大的惊吓般向后退了一步,手里的保温盒坠落在地,热汤溅了一身。
“啪”的一声,程兆川高高扬起手,竟重重给了小男孩一巴掌!
“不长眼的野小孩,要是吓到昭昭肚子里的孩子,我和你没完!”
“洛桑!”
2
我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忍着疼翻下床,将男孩抱进怀里。
“道歉。”我看着男孩脸上肿起的红痕,心如刀割,仰面对程兆川冷声道。
“谢姐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许昭意眼圈一红,忽然跪下来,朝我砰砰磕起头:
“我不该出现在这里让你烦心。兆川也是太紧张了所以才会动手,你有气冲我来,别怪他。”
“昭昭!”程兆川心疼地护住许昭意,看向我时眼中寒意刺骨,道:
“昭昭知道你没事后忍着孕吐也要爬起来给你做补汤,可你非但不领情,还要纵容别人伤害她!”
“谢云卿,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只要你安分守己,好好照顾昭昭直到她生下孩子,程夫人的位置就依旧是你的。”
我听着他仿佛施舍恩赐般的话,心中只觉得又好笑又悲凉。
“我说过了,我早就不要这个位置了。”我直视着程兆川,对他一字一句道:
“我要和你离婚,而你,现在要给洛桑道歉。”
程兆川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过了许久,方轻蔑地笑起来:
“离婚?谢云卿,你舍得吗?”
“既然你不愿意回去,那就在这里照顾昭昭。”他随手一指,道:
“方才昭昭的衣服被汤弄脏了,你现在就去卫生间洗干净。”
“用你那只完好的右手。”
说罢,他不顾我和洛桑的挣扎,直接将我推进了卫生间。
一件厚重的羽绒服被扔了进来,程兆川打开水龙头,将我的手摁向冰冷刺骨的水流。
然后他反锁了门,将我关在里面,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呼救,让我听着他与许昭意隔着门板动情接吻,放肆嘲笑:
“别管她,她性子一向娇纵,比不上你万分之一,是该给些教训。”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最终力竭昏迷,倒在了阴冷的卫生间里。
好在梁牧派来照顾我的人及时赶到,将我救了出来。而我转醒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带我转院。
我不想再看到那张脸,只想养好身体,然后迅速与他了断。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八年爱意,原来也会如雪崩一般,转瞬坍塌。
我在另一家私人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期间拉黑了程兆川的所有电话,然后拟好了离婚协议。
而一个星期后,我强撑着还未好全的身体回到了家,却看见了站在客厅的程兆川。
“哼,你终于舍得回来了?”程兆川冷嘲热讽,而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当即打了电话给梁牧的人,让他们来帮我搬家。
“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程兆川陡然起身攥起我的手腕,而许昭意竟从我的卧室里走出来,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道:
“谢姐姐,我刚刚不小心把你的瓶子打碎了,但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垃圾都冲进马桶里了。”
“我和兆川哥哥现在就走,你别生气。”
我的心一沉,冲到卧室,却看见了一地碎片。
那是我放在柜子顶端的一个小瓷瓶,而里面的东西已经被许昭意故意扫净,冲进厕所。
仿佛万箭穿心,我回过身,照着许昭意的脸就是一巴掌。
“昭昭!”程兆川冲过来,猛地将我推倒在地,我的手掌扑在那堆碎片上,当即血流如注。
可我,却好似感觉不到疼了。
“谢云卿,你发什么疯,那不过是一个积了灰的瓶子!”
他冲我吼道,而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扯了扯嘴角,对他道:
“程兆川,那是孩子的骨灰。”
3
程兆川愣了一下,看向地上的碎片,没有说话。
“滚出去。”我头痛欲裂,情绪濒临崩溃:
“现在,滚出我的房子!”
许昭昭被我吓得浑身一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而程兆川立刻搂住她,脱口而出道:
“装什么啊谢云卿,你有那么爱孩子吗?”
“你就是因为对别人的孩子太掏心掏肺,所以才留不住自己的孩子。”
我浑身一震,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当年我为了救一个学生发生意外,失去了我和程兆川的第一个孩子。
而我醒过来后,是他抱着我,让我不要自责,说都是因为他没有照顾好我们才会发生意外,他永远支持我的事业。
正是因为那些温柔又坚定的话语,我才缓过了丧子之痛,告诉自己向前看。
而如今,他将我心上最深的那道疤揭起,将它践踏得血肉模糊,用那样诛心的话攻击我。
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可怖,程兆川眼中也闪过一丝懊悔,不自在地咳嗽了一声,道:
“昭昭也是无心的,但事情已经发生就没办法,你想要什么补偿,我可以……”
“把字签了吧。”我站起身,如一具行尸走肉般将床头柜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我当然爱我的孩子,但我不再爱你了。”
“房子你们想住就住吧,我今天就离开。”
程兆川看着眼前的白纸黑字瞪大了眼,立刻将那份文件夺过来,当着我的面,烦躁地撕碎了它。
“我说过了,收起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没用的。”
“你现在演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和奶奶诉苦,说我和许昭意欺负你?”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还想当这个程夫人,就和我们一起回去。昭昭生下的孩子以后对外就称是你的孩子,这样够给你脸面了吧?”
他将废纸照着我的脸甩过来,而我转过身,一言不发地向外走。
“谢云卿!”程兆川语气加重,还要追上来,许昭意就发出一声痛呼:
“兆川哥哥,我肚子疼……”
程兆川即将碰到我的手瞬间收回,焦急地回到了许昭意身边,将她抱起。
而我已经不在乎了。
崩塌的雪,碎裂的瓷瓶,一切都在告诉我,我早就应该抽身离开了。
梁牧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对着那份再次被退回的离婚协议发愁。
“他不肯签字。”
“那就让我来。”梁牧的声音坚定低沉,对我缓缓道:
“我手上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就去接你。”
“我已经知道他做的那些事了。所以哪怕你最终选的人不是我,我也绝不会让他再纠缠你。”
“放心交给我,好吗?”
我听着他的声音,一颗心也慢慢安静下来。
仿佛有魔力一般,从认识梁牧的第一天起,他总是能让我安心。
当初醒来直接答应他有一半的原因是一时冲动,可现在看来,或许同他在一起,也是上天给我的指引。
于是在和梁牧通话结束后,我想了想,还是拨通了程老夫人的号码。
4
老夫人听说我要离婚,当即就要去找程兆川算账,让我不要冲动,再考虑考虑。
但我去意已决,她见我如此坚定,最终也不得不叹了口气,道:
“当初你救了我,我本让兆川任你当妹妹,可他却不肯,执意要娶你。”
“我老了,见你们两个情投意合,便也极力撮合,可后来才想起来,他和那个什么许昭意当年也是在雪上彼此认识的,而且穿的衣服和你那天救我时几乎一模一样。”
“我本想直言,但他那样执着,我就以为这不过巧合,他早就忘了那个女人,全心全意地爱你。”
“可现在看来……”
老夫人悠悠地叹着气,而我愣在原地,过了良久,才自嘲般地苦笑一声。
原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或许是雪山上的神明见我被蒙蔽了太久,所以才用这一场雪崩让我彻底清醒。
既然如此,当断则断。
虽然梁牧说会帮我,但我还是换了一个新的住处,独自办理了离婚登记,开始准备诉讼离婚。
可我没想到的是,我还未等到他,程兆川就先把我绑到了医院,逼我跪在许昭意的床前。
“谢云卿,你果然和奶奶告状了,所以她老人家才会让人找到昭昭,逼着她到医院打胎!”
程兆川怒不可遏地将手机摔到我的脸上,我的额角被砸出了血,听着许昭意断断续续的哭声:
“谢姐姐,等我生下孩子,我就离开,再也不会打扰你和兆川哥哥的。”
“但你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它只是一条无辜的生命,求求你,别伤害它!”
许昭意愈哭,程兆川就愈愤怒。而程兆川的妈妈不知何时也来了这里,正心疼地搂着许昭意,骂道:
“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程家的长孙,我看谁敢赶你!”
“一只不下蛋的母鸡罢了,天天待在这破地方家也不回,哪里配做我们程家的儿媳妇?”
程母对我常年待在藏区支教一事一直十分不满,如今找到理由,更是开始放肆羞辱贬低我。
而许昭意侧着脸,在没人发现的位置对我一笑,眼里满是得意。
“我只和奶奶说了离婚的事情,她也同意了,不可能找人绑架她。”
我强忍疼痛镇定辩驳,可程兆川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竟直接喊来几个保镖,把我押到了医院前的空地。
“把她的衣服扒光了,让她跪在雪山前,好好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
“程兆川,你疯了!”我死命护着自己的领口,可保镖力气太大,压着我,直到我身上只剩一件针织衫。
寒风刺骨,头上的血混着我的冷汗滑落,我望着他冷漠的脸,只觉得呼吸愈发粗重,几欲晕厥。
而下一秒,一块石头就砸在了程兆川的身上,随后,是更多。
“大坏蛋,离我们老师远一点!”
我的学生们从另一侧冲过来,手里拿着树枝和石头狠命地朝程兆川砸去,牢牢地挡在我的面前。
一架直升机带着轰鸣声降落在医院前的空地上,梁牧拉开舱门,飞速向我跑过来。
“我来迟了。”他心疼地将外套披在我身上,安抚着我,看都没看程兆川一眼,将我打横抱起,便向身后的一辆房车走去。
“站住,你是谁!”程兆川恼羞成怒地冲过来,而刚从直升机上下来的程老夫人迎面给了他一巴掌,喝道:
“不肖子孙,还不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