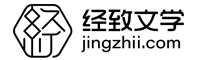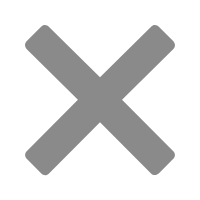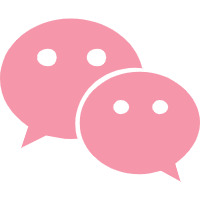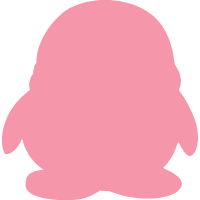-
家人被杀,夫君要我打一百零八道烙印赎罪!
本书由经致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山贼将家中奴仆屠尽,还掳走了公婆。
我逃出生天,找在县城做官的夫君傅迟砚求助。
他温柔安抚了受惊的我一整夜,
在我熟睡之后,却将烧红的烙铁放在了我的背上。
我因剧痛发出惨叫时,他无情冷笑。
“我以为像你这么狠心的女人是不知道痛的。”
“可你这点痛,与我家殒命的一百零八口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说,为什么只有你能活着?”
他挑断我的脚筋,让我这辈子都别想逃。
整整三个月,我看着他与小青梅郎情妾意。
而我则带着镣铐被他像狗一样拴在房门外,日日听他们欢好。
傅迟砚要在我身上打下一百零八道烙印,尝尽他家人受得苦。
让我整夜整夜的放血抄佛经,为他死去的家人祈福。
他是如此恨我,却在夜深人静时悄悄为我上药。
“你就是仗着我心软,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勾结山贼?”
我在他纠结的爱恨中日渐崩溃。
不过,很快我就能解脱了。
山贼给我下了消魂散,百日内没有解药,我就会毒发身亡。
如今,只剩下三天。
……
已经午夜,柴房门被人粗暴的踹开。
府中管事的张嬷嬷一把将我揪起来,狠狠给了我几记耳光。
“小姐还在辛苦伺候姑爷,你这个奴婢怎么睡得着?”
她扯着我的头发,骂骂咧咧拖着我往外走。
背上的烙印裂开,在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傅迟砚皱着眉头看向我身上的血迹,皱起了眉。
“月儿要沐浴,你去准备热水。”
我抬眼,看着胡枕月脖子上的点点红痕,和敞开的衣襟中若隐若现的胸。
傅迟砚抬脚踹向了我的胸口。
“月儿也是你这双脏眼能看的?还不快去。”
我忍痛低头道歉:
“奴婢知错!”
慢慢用手爬向门外,却听到傅迟砚在身后吩咐:
“谁都不许帮她!”
我只觉好笑。
这个府里有谁会帮我?
等我烧好一桶热水,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汗液浸到背后的伤口,让我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
胡枕月用手试了试水温,嫌弃道:
“太凉了,你是想冷死我?”
我低头解释:
“奴婢手脚不便,厨房离这里又远……”
胡枕月面色一冷:
“你这是在怪我?”
“一个奴婢,主子要你做什么你还敢推诿?”
张嬷嬷立马抽出鞭子,将我抽得在地上直打滚。
鞭子上的血溅到了胡枕月的衣服上,她尖叫一声,跳进了傅迟砚的怀里。
“我怕血……”
傅迟砚轻柔的抱着她,对我冷声道:
“滚出去!”
我艰难地爬出了房间,身后是傅迟砚温柔的安慰:
“吓到了吗?还怕不怕?要不要叫大夫来给你开一副安神汤?”
我心里一阵酸涩,早就没有知觉的双腿此时却有些隐隐作痛。
嬷嬷兜头给我浇了一桶冷水,脸上尽是嫌弃。
“把身上的血洗干净,别熏着小姐。”
她又将一块脏臭的抹布扔在我脸上:
“地上的血迹也擦干净,否则有你受的。”
我顶着二月的寒风,擦了大半夜地板上的血。
路过傅迟砚门口时,听着里面传出来的暧昧声响。
还是没忍住掉下一滴眼泪。
不过,很快我就能解脱了。
还有三天,我就会死了!
太阳升起,府里的下人们开始新的一天忙碌。
傅迟砚一脸餍足的走出卧室,看着睡在廊下的我直皱眉。
“一大早又脏又臭的真晦气!”
我赶忙低头道歉:
“奴婢知错,这就收拾干净!”
爬过几个扫地的粗使丫头时,一口浓痰吐在了我脸上:
“呸,这么个坏东西昨天还敢问管家嬷嬷怎么让少爷高兴?”
“看到她我就想起少爷死去的家人,如果不是她,少爷怎么会家破人亡,孤苦伶仃?”
我只想赶紧离开,身后的傅迟砚动作更快。
他将我拖到了处罚下人的刑房,将我用链子吊了起来。
看着旁边烧红的烙铁,我的身子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
傅迟砚拿着烙铁,拨动着火炉里的烧得正旺的炭火,面无表情。
“沈青蘅,这些日子过得舒坦吧,我已经十天没有审问过你了。”
“说,你到底是怎么勾结山匪,屠我满门的?”
我的身体已经下意识抖起来:
“我没有!”
话音刚落,傅迟砚手上的烙铁就落在了我的胸口。
皮肉烧焦的臭味直钻鼻腔,我全身痉挛,撕心裂肺叫喊起来。
动作太大,背后的伤口再度崩开,鲜血顺着下身滴落,在脚下汇成了一摊。
直到傅迟砚收回烙铁,我的身体还在颤抖。
傅迟砚有些恼怒,他捏住我的下巴,又问了一次。
我吐出一口鲜血,只觉五脏六腑都在叫嚣着疼痛。
“我没什么好说的。”
没做过的事情我要怎么说?
“你的嘴还真是硬。”
他拍了拍手,下人就端进来两个牌位,是我父母的。
“你要做什么?”
我心里一阵发慌,声音都在颤抖。
这两个牌位是父母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
“你不肯说我只好给你下点猛药了。”
他冷眼看着我的表情逐渐失控,将牌位一个一个扔进了炭火里。
“不,不要!爹,娘!”
我绝望的嘶吼,却换来他的嗤笑:
“自己的爹娘连牌位都看得这么重,那我的父母呢?”
“你勾结山贼屠戮他们的时候,有想过他们也是我唯一的父母?”
“沈青蘅!他们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勾结山贼?为什么要害他们,说!”
我的牙齿将下唇咬得血肉模糊,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还敢狡辩!”
傅迟砚一巴掌甩过来,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一丝热流从耳朵流出。
“傅迟砚,你为什么不信我?”
“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我猛地一口咬向舌头,想自我了断。
傅迟砚动作很快,他用手捏住我的嘴,我的牙齿狠狠咬住了他的虎口,鲜血直流。
“沈青蘅,没有我的允许,你敢寻死?”
几记重重的耳光扇到我的脸上,我晕了过去。
我在疼痛中醒来,就看见傅迟砚正脱掉我身上带血的衣服,给我上药。
衣服和血痂长到了一起,每掀起一块的痛苦都不亚于凌迟。
我想躲,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他端起一碗药,递到我的嘴边。
“沈青蘅,在我没让你死之前,你不许死!”
或许是之前的自尽吓到了傅迟砚,他少见的给了我一些温情。
我撇开头,并不想喝。
反正山贼下得毒药马上就要发作了,喝这些有什么用?
我麻木的笑。
“傅迟砚,你让我死吧!”
这个死字似乎触到了傅迟砚的忌讳,他一下就发了疯。
他捏住我的脖颈,将一口药渡了过来。
苦涩的药味中泛着淡淡地血腥味。
他的吻激烈而粗鲁,几乎要将我吞吃入肚。
我恍惚想起我们以前是多么相爱。
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第一次见到傅迟砚的时候,才三岁。
他就指着我对傅母说:
“娘,我要这个妹妹做我的新娘子。”
几位大人都被逗得开怀大笑。
虽然是句童言,两家父母却当了真,当下就定下了亲事。
直到我十五岁那年,傅迟砚高中状元,被公主看中。
皇帝要给他赐婚,他拒绝了。
“臣已有婚约,是臣爱慕多年之人,不能辜负。”
他被贬出京城,做了一个偏僻县城的县令。
我为他不值,他却笑了笑。
“为了阿衡,值得!”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蜜糖浸满。
后来我们顺利完婚,我的父母却在不久后遭遇山贼,死于非命。
我当时哭到晕厥,是傅迟砚紧紧抱着我,说以后有我,我的爹娘就是你的爹娘。
我一心想给父母报仇,机缘巧合之下收买了一名当时害我父母的山贼中的一员。
本想与他里应外合,将这些山贼一网打尽。
可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山贼找上了傅家。
傅家满门被屠,傅父和傅母也被掳走。
我被他们下了消魂散,去筹集赎金,如果在百日内不回来,就会毒发身亡。
当时的傅家就逃出来我一个,所以傅迟砚怀疑上了我。
他认为是我勾结山贼,害他家人。
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予理会,认定了我是罪魁祸首。
不过,也没有关系了,我很快就能解脱了。
傅迟砚的手指在我身上游走。
在摸到烙印的时候,他突然停下了。
我冷笑,扯开自己的前襟。
那里密密麻麻全是傅迟砚打下的烙印,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肤了。
“傅迟砚,对着我这样的罪人,你还下得了嘴?”
他果然恼怒起来,声音像淬了冰。
“沈青蘅,你别想激怒我。”
“想求死,没门!”
他将我拖到了他的卧室内,用铁链锁在床前的脚踏上。
隔着一层薄纱,胡枕月依偎在他怀里,看着我的眼神却射出恶毒的光。
她用唇语说:
“沈青蘅,你该死!”
我蜷缩在地上,迷迷糊糊的睡着。
半梦半醒间,似乎有人在轻轻摸我的头发。
温柔又爱怜。
“阿衡,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该多好!”
是傅迟砚吗?是他在心疼我吗?
我努力睁开眼,却只看到满室漆黑。
张嬷嬷拉着我的链子,将我拖到了院子里。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我穿着单薄的秋衣,风一吹冻得瑟瑟发抖。
胡枕月穿着白色的狐毛披风,拿着暖炉,对我笑得温柔。
“沈姐姐,听说你写的一手好字,如今我身怀有孕,还请你替我抄几份佛经安胎。”
我震惊的看向她。
她竟然已经有了身孕?
胡枕月的眼神中有些得意。
“沈姐姐,你也为我感到高兴吧,你为我抄佛经,傅郞也一定很感动的。”
见我不动弹,张嬷嬷一脚踢向我的肚子。
“怎么,嫉妒我家小姐,谁让你自己不争气?如今惹了傅大人的厌弃,还不将功赎罪?”
我倒在地上半天缓不过来,被她拖到书桌前。
我脚筋已断,她便让我跪着写。
等我颤抖着拿上笔,却发现桌上没有砚台。
胡枕月嘴角勾笑,善解人意的解释:
“抄佛经要的就是心诚,沈姐姐不是早就知道以什么为墨最合适?”
张嬷嬷扔了一把生锈的小刀在我面前。
我小声辩解:
“这刀太钝了!”
张嬷嬷啐了一口:
“小姐怜惜你,你还挑三拣四,多割几次不就行了?”
我不再言语,用刀割了几次才割开一条流血的伤口。
血流出来很快就凝固了,我只好写完几个字,就停下挤压伤口。
一道伤口流不出血,我只能重新划开一条。
小小一页佛经抄完,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十条伤口。
胡枕月拿起我抄的佛经一看,撇了撇嘴。
“沈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心中对我有怨言,但是我肚子里是傅郞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能这么害他。”
“佛经抄成这样,万一佛祖怪罪报在孩子身上,你担待得起吗?”
我的手冻得麻木,笔都握不稳,字写得有些扭曲。
正想解释,傅迟砚却突然过来了。
胡枕月像见到了救星,泫然欲泣的扑到傅迟砚的怀里。
傅迟砚低声安慰了几句,身边的嬷嬷赶紧将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他。
他神色一冷,将我掀翻在地,一脚踩在了我的手上狠狠碾了几下。
“这双手既然字都写不好,那也没什么用了。”
我痛的尖叫出声。
以前,傅迟砚最宝贝我这双手。
我这双手,能为他弹琴,为他研墨……
要是不小心碰了磕了,他都会心疼半天。
如今,他却将它踩在泥里,甚至还想碾碎它的骨头。
“也许沈姐姐只是累了,傅郞不要怪罪她。”
胡枕月温柔的劝住了傅迟砚。
“你呀,就是这么心软善良。”
傅迟砚缓下脸色温柔的抱住她,冷冷的看向我。
“给我滚回柴房,别在这里碍眼。”
莫名的,我早已麻木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
我什么都没说,慢慢的爬回柴房。
身上的伤口被磨破,流了一地的鲜血,被打扫的丫头咒骂了一路。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张嬷嬷一鞭子抽醒。
“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
“小姐的胎要是有事,你几条命都不够赔。”
原来,胡枕月肚子疼,出现了轻微的流产迹象。
他们认为是我白天的佛经抄的不好,惹的佛祖生气,才惊了胡枕月的胎。
我百口莫辩,只能认命承受她的鞭子。
几十鞭下来我渐渐承受不住,傅迟砚出现制止了她。
我以为他不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却看到他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身后带着一名大夫模样的人,手里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
“沈青蘅,没想到你这么嫉妒月儿。”
“怎么,你不会还觉得我的孩子会从你肚子里生出来吧?”
“真是痴心妄想,你这么狠毒的女人,不配做母亲。”
他一挥手,身后的奴仆就上来摁住我,那个大夫模样的人捏住了我的下巴。
将那碗黑乎乎的汤药尽数倒进了我的嘴里。
我呛咳不止。
“咳咳,傅迟砚,你给我吃了什么?”
“绝子汤,你这辈子都做不了母亲了!”
一股热流从我的下身流出,我腹中剧痛不已,蜷缩在地上。
傅迟砚厌恶的看了我一眼,示意身后的大夫上前给我诊脉。
“看看药有效果没有,不行的话再给她来一碗。”
大夫摁住了我的脉,诧异道:
“大人,她这是流产的迹象!”
“什么?!”
“她已有三月身孕,不过眼下是保不住了。”
听完,傅迟砚的脸蓦得黑沉如炭。
“我离家四月,你为何会有三月身孕?”
“沈青蘅,你之前口口声声说你是无辜的,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
“与人私通,还珠胎暗结,害我家人父母!”
“一桩桩,一件件,你十条命都不够赔!”
我努力张嘴想解释,但是却被痛的开不了口。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傅迟砚吩咐道:
“打下来的贱种拿去喂野狗!”
我心中一痛,挣扎道:
“傅迟砚,你不能这样,那是你的孩子!”
傅迟砚冷笑一声。
“孩子?我的孩子在月儿肚子里!”
我心如死灰,在剧痛中陷入了黑暗。
我做了个梦,梦中有个小孩子浑身是血,被一群野狗追赶。
他哭着朝我喊。
“娘亲,救我,我好怕,野狗咬得我好痛。”
“娘亲!”
“不!”
我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却在床边看见了一个我熟识的人。
是我的乳母李妈妈。
她看着我一身的伤,心疼的只落泪。
“小姐,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带着哭腔依偎进她怀里。
“李妈妈,我好痛!”
“小姐,别怕,我这就给你去拿药,我去求姑爷。”
她还未来得及起身,傅迟砚就沉着脸进来了。
李妈妈噗通一声跪下。
“姑爷,求您行行好,给小姐上点药吧,你以前可是最疼小姐的!”
“以前?那是我鬼迷心窍,引狼入室,把蛇蝎当珍宝!”
傅迟砚一挥手,几个奴仆就把李妈妈抓了起来。
“沈青蘅,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和谁勾结害的我们家?”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一如既往的嘴硬,既然你不说,那你身边的人就有罪受了!”
傅迟砚拿起一块烙铁,就往李妈妈的胸口一放。
李妈妈霎时惨叫起来。
我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
“求求你,不要折磨她了。”
“她已经快六十岁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要折磨就折磨我吧!”
傅迟砚眼神冷的像冰。
“说,你到底是怎么与人勾结的?”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撕心裂肺,恨不能将心掏出来给他看。
我真的没有骗他。
“还敢嘴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傅迟砚拿出一把匕首,在李妈妈身上捅了一刀。
李妈妈的尖叫愈加惨烈。
我已经嗑得满脸都是血,哭着哀求。
“我真的没有,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傅迟砚失去了耐心。
“既然你不说,那就也让你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
他猛地将手中的匕首刺进了李妈妈的心脏。
一切发生的太快。
李妈妈只来得及看我一眼,就没了声息。
我的心中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仿佛那把刀刺进的是我的胸口。
李妈妈是我最后一个亲近之人,她苦了一辈子,前不久刚刚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
都是我害了她!
我心中的恨意第一次如此浓烈,如果眼神是刀,傅迟砚早就被我千刀万剐。
“傅迟砚,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你会害死你父母的!”
“傅迟砚,我恨你,恨死你了!”
傅迟砚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道:
“沈青蘅,你终于说了实话,你果然恨我!”
他还想教训我,却被一个仆人匆匆叫了去。
胡枕月肚子有些疼,他急着去看她。
“等看过月儿,我再来找你算账!”
我嘲讽的笑了。
再找?你只会找到我的尸体。
我仍然被锁进柴房,看着那块巴掌大的窗户,心如死水。
门外的奴仆们步履匆匆,为了满足胡枕月的一切要求来回奔波。
我蜷缩在角落里,感受着毒发深入骨髓的疼痛。
真好,我就要解脱了!
到了下半夜,胡枕月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
兵荒马乱的府邸终于安静下来。
傅迟砚长舒一口气,正准备喝口茶润润喉。
一名仆人神色怪异的进来禀报。
“大人,门外有人找您……”
傅迟砚不甚在意的将茶送到嘴边。
“什么人?”
“他们说,是您的父母!”
茶杯落在了地上,碎成了几片。
傅迟砚疯了般赶到门口时,衣衫褴褛的傅家父母正相互依偎取暖。
还没等傅迟砚激动上前,傅父就拦住他。
“青蘅呢?她在你这儿吗?她中了毒药,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快给她找大夫。”
傅迟砚心中咯噔一下,却不以为然。
“她勾结山匪,我把她关进了柴房,还好好的呢!”
傅父如遭雷击,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快告诉我柴房在哪儿?”
傅迟砚有些不情愿的在前带路,推开柴房的门。
“爹娘,你们看吧,沈青蘅没事。”
傅家父母只看了一眼,就崩溃的大喊“快请大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