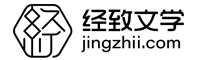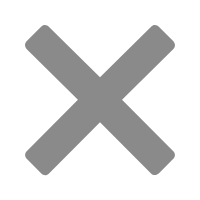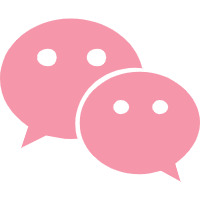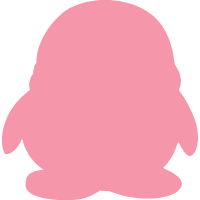-
深潭不见
本书由经致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这是我陪潭林北漂的第八年。
他说等他当上大导演,就让我做她的第一个女主角。
我为此心甘情愿地托举了他八年。
他也如愿成为了当下最受瞩目的导演之一。
私人晚宴上,潭林即将官宣他成名后要拍的第一部电影,以及他的第一个女主角。
我强忍着激动的泪水,时刻准备好上台。
“接下来,有请我的女主角——”
“周言雪。”
我脚下的动作顿住,诧异地望向舞台上的他。
因为我不叫周言雪,我叫陈以澜。
01
为了今天这一刻,我足足等了八年。
这是八年以来,我唯一能向大众完全展示自己的机会。
潭林站在台上,少见的长发背头造型,一身藏蓝色的单排口西装,是两个月前我陪他去海市定的。
他脖子上那条H家的印花领带,是我送他的贺礼,也是今天早上我亲手为他系上的。
可现在本该站在他身旁的我,却变成了别人。
潭林看向她的眼神,温柔里还带着难以掩盖的欣赏。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
“非常感谢潭导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一定会加倍努力,不辜负潭导对我的期望。”
周言雪站在聚光灯下,那张漂亮的脸蛋笑起来,可爱又不失优雅。
热烈的掌声响起,只有我独自沉默在这片喧哗中。
大脑趋近空白,胸腔里的心跳声反而震耳欲聋。
我认得周言雪。
她是最近热播剧《再见十五次》里的女配角,因为人设招人喜欢而爆火了一段时间。
我怎么会不认得周言雪。
她是潭林曾经的追求者,是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穿着婚纱向他求婚的疯狂追求者。
而此刻,他们身穿礼服并肩站在舞台上,构成了一幅我不曾幻想过的陌生模样。
两个人就好似两把生锈的钝刀,直直捅进我的喉咙里。
令我窒息,令我同溺水般窒息。
我不死心地抬头望向潭林。
他的视线掠过台下的每一张脸,也没为我多停留半秒。
顷刻间,裙子的一角被我拽得起皱。
在这个众星云集的地带,没有人知道陈以澜是谁。
潭林知道,但他好像不在乎了。
02
室外的露台很宽阔。
凉爽的风迎面吹来,我才得以大口喘着气,仿佛要把所有痛苦都吐出来。
“以澜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闻声一震,转头看去。
玫瑰金色调的礼裙,步伐带动裙摆的摇曳,如洒满月光的湖面荡起涟漪,波光粼粼。
是周言雪。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条老套的黑色礼裙,不禁自讽地笑了,笑声化作一声叹息。
她确实比我更像今晚的主角。
周言雪走到我面前,直接抬起我的双手握住。
开口就是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以澜姐,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责怪阿林哥。”
阿林哥……
我都从没这么叫过他。
周言雪的目光低垂,模样显得楚楚可怜。
“是投资方那边指名要我当女主角,不然就撤资,阿林哥也是没办法。”
“以澜姐,你知道的,阿林哥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这部电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她一字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但很是难听。
这个我曾以为与我们再无交集的女孩,现在正在替我男友向我求情。
有些好笑。
如果我不成全和原谅他们,倒显得我才是那个罪人了。
我忍不住低笑一声。
“你不用担心,这是我和他的事情,我会听他亲口说。”
我缓缓将手抽离,指节一寸一寸滑出她的手心。
周言雪的双手悬在原处,不甘心的“嗯”了一声,悻悻把手收回。
紧接着,露台的玻璃门被打开了。
潭林站在门口,挺拔的身影立成一条直线。
他一只手扶在门框上,语气平淡:“言雪,经纪人在找你。”
他们相视一眼,默契的什么也没有说。
周言雪冲我莞尔一笑:“以澜姐,我先走了,期待下次和你见面。”
我轻点下头,回以一个礼貌的微笑。
最好再也不要见了。
我转身面向花园,潭林从背后轻轻搂住我的腰。
他温热的呼吸中夹杂着些酒气。
“以澜,对不起,为了得到投资,我没有别的办法。”
“等这部电影成功了,我一定……”
潭林,如果这就是你的答案,那我宁可不听。
“别说了。”
我有些哽咽,强忍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从容。
“我想回家。”
潭林连声答应着:“好,回家,我们回家。”
可他似乎忘了,我们根本没有家。
03
大学毕业以后,我不顾父母和朋友的劝阻,义无反顾地跟着潭林去到了北市。
我们怀着各自的目标来到这里。
我学表演,梦想成为演员,潭林学编导,梦想成为导演。
白天我们是看似光鲜亮丽的艺术工作者,晚上却蜗居在不到30平的出租屋里。
两个人挤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潭林抱着我,我蜷缩在他怀里,彼此身上廉价的洗发水味和被子里散发的霉味时常混合在一起。
他喜欢抚摸我的脸和头发,声音轻柔得如风拂过我耳边。
“以后我会买个大房子,买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我鼻子一酸,脸埋进他胸口,眼泪打湿他的衣服。
“以澜,我想拍一部关于北漂人群的纪录片。”
我正要说好,又听见潭林说:“起码需要50万。”
老旧的风扇在一旁嘎吱作响,许久都没有人再说话。
我忽然坐起身,转头对他笑。
“好,拍吧。”
“你放心去做,剩下的交给我。”
我看过潭林学生时期的一些作品。
他镜头下的故事很像一杯冷掉的茶,回味苦涩绵长,看完总是怅然若失。
可能这就是我为他执迷的原因。
在我眼里,潭林一直是个才华洋溢,能力出众的人,所以我始终愿意相信他。
但当理想和现实矛盾时,不得不有一方为之妥协。
我的演艺生涯从跑龙套开始。
不管戏多戏少,戏好戏坏,只要能演,我就知足了。
我拼了命想挣钱,长时间不停歇的工作,直到身体垮掉,不拍戏的日子都在医院打着吊瓶度过。
可就算我把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部攒起来,也远远不够那50万。
我在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几年,好不容易才为潭林争取到一个机会,我们却差点因此闹僵。
04
“你想当导演?”
说话的是业内著名的制片人吴令老师,也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小伙子挺有志气。”
我和潭林的手在桌下紧紧扣在一起,才刚刚松了口气,转眼就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年轻人有理想是好事,但我看还是先想想怎么凑够器材押金吧。”
全场哄然大笑。
潭林憋得脸都红了,如果不是我拉住他,他根本不管什么制片人大导演,站起身就走出这个有去无回的门。
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受这种委屈。
只可惜家里的花瓶,潭林刚进门就把它打碎在地。
“妈的,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别这样,潭林,只要我们更努力一点,他们总会看到我们的价值的。”
我走上前握住潭林的手,却不料被他一把甩开。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没本事?”
潭林回头看我时,眼眶泛红。
我摇着头:“没有,我从没这么想过。”
他一步一步朝我走近,我一步一步往后退。
直到脚后跟触到地上的花瓶碎片,我无处可躲。
潭林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将我拉到他跟前。
我们四目相对。
他那双黑得像一口枯井的眼睛近在咫尺,近得让我害怕。
“那个叫唐寒的摄影师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他的嗓音低哑,携着浓重的酒气。
“他看你一眼脸就红得不像样,感觉随时都要去了。”
我用力摇着头:“唐寒对酒精过敏,所以脸容易红,看我也只是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几次……”
不等我过多解释,潭林的唇舌一下撞上来,呛人又酸涩的啤酒味袭来。
他掐住我脖子的那只手,力道也不受控制地越变越大。
我疼得快要昏厥过去,艰难地从喉腔里挤出一句:“潭林,我明天还有拍摄。”
他回过神来,猛然松开了手,略显慌乱。
“对不起,以澜。”
我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不浅的痕迹,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能戴着丝巾出门。
潭林对此感到很愧疚,但我何时真的怪罪过他。
整整八年,劣质酒精一样辛涩的八年。
就这样被我们熬过去了。
万幸的是,我们倾尽了所有才完成的这部纪录片,让潭林一举成名了。
潭林初次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丝毫没有怯场。
他挺胸抬头,目光沉稳,发言时也从容不迫。
那个站在舞台上熠熠发光的男人,从此在我心中难以抹去。
此后,我们再也不用回到那个阴暗潮湿的出租屋,而是回到这个宽敞又明亮的家。
05
潭林有些醉了,还在屋门口就急不可耐地把手伸进我的体恤里。
离开宴会时我特意更换了服装,没想到却是方便了他。
“我们有段时间没做了。”
潭林一边扯自己的领带,一边吻上来。
他的吻来势很凶,而且探得很深,总是吻得我头皮发麻。
口腔里弥漫着香槟的味道,那是一种尖锐的酸,像玻璃渣裹着蜂蜜滑过喉咙。
“以澜,你帮我脱。”
潭林把我摁在墙上,就这么居高临下地盯着我,等待我主动褪去他身上的衣物。
见我一直不动,他把脸埋进我的肩窝里,略带撒娇地说:“我没力气了,你帮我脱好不好?”
说这话的时候,潭林的手掌还紧紧扣在我的腰上,正有预谋地顺着我的大腿往下滑。
我没有作声,任由他的动作不停。
他抬眼看着我,是一副不想再隐忍的表情。
潭林将我横抱起来,走进了房间里。
由于酒精的缘故,潭林全身都在发烫,哪里都烫得不行。
他不停在我腿间磨蹭,齿缝中吐出低沉的喘息。
眼看他就要顶进去,我却叫停:“等一下,潭林,你还没戴。”
他像是没听见似的,掐着我的大腿强行顶了进去,喉间压抑的闷哼一声。
两行泪水倏地涌出来,滴落在枕头上。
看见我的眼泪,他才仿佛清醒了一般,趴在我耳边轻蹭:“别担心,我不会弄在里面的。”
我伸手抵在潭林的肩膀上,硬生生将他推开。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停下来愣愣地看着我。
“今天是怎么了?你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他抬手用指腹拭去我眼角的泪。
我别过头,眉头拧在一起。
“吃了药身材会走样,我还有戏要拍。”
潭林听后,脸色一下就变了,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从我身上离开。
“你不想做了就直说,别搞这么麻烦。”
他走到桌边,抓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来含在嘴里。
潭林的身子永远保持着挺立,低头点烟时都只折颈,不弯腰。
“潭林。”
他依在桌边,侧头看我:“嗯?”
“你和她睡了吗?”
烟雾萦绕在他四周,我看不清他的脸。
“回答我。”
但我知道,我的表情一定像烟灰缸里那些干瘪的烟头,皱缩着很难看。
潭林掐灭烟头,走到床边俯视着我。
他的表情和语气都冷。
“睡过,睡过好多次,你满意了吗?”
06
大学毕业典礼那天,周言雪穿着一身纯白的婚纱出现在学校广场上,在一众黑色的学士服之间格外引人注目。
“潭林,我喜欢你,是想跟你结婚的那种喜欢。”
她把一枚戒指放在潭林的手心,并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如果你同意跟我在一起,就亲自为我戴上。”
旁观的许多人都在为她的坚定和勇气感叹。
当然,也有人说她是个疯女人。
可在我看来,是她的盛开违背了这个人人都在告别的季节。
潭林越过嘈杂的人群走到我面前,他递给我一束百合花,颜色同周言雪身上那条婚纱一样洁白。
他说:“以澜,跟我去北市吧,我想在那儿跟你有个家。”
至此,这场披着一种名叫浪漫外皮的闹剧,最终以周言雪撕烂她身上那条婚纱和我笑着捧起那束百合花结束。
我注视着眼前冷漠的男人,他的笑颜一瞬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个青涩且真挚的少年,好像早已不复存在。
潭林背对着我坐在床边,深色的皮肤下能看见青绿色的血管,背上薄薄的肌肉随呼吸缓慢滑动。
我很庆幸他此时看不见我这张惨白的脸。
“可是潭林,我们不是说好了明年就结婚吗?你为什么……”
他的声音平静而淡漠:“你随时都可以反悔。”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周言雪身上那条破损的婚纱原来早就穿在了我身上。
而如今,又到了百合花盛开,人人说着分离的季节了。
“那我这八年,算什么呢?”
我深知在感情里问为什么的人,都得不到一个好结果。
可我就想要个结果。
“对你来说,我又算什么呢?”
07
房间内很安静,偶尔传来空调低频的嗡嗡声。
我还在等他回答。
“是,这八年来你辛苦了。”
潭林仰起头,闭目长叹了一口气。
“但我跟她睡了,也是事实。”
我的心一沉,呼吸断在唇边。
“那是因为我们平时很难见面,她又缠了我这么久,我正好跟她玩玩,仅此而已。”
只是仅此而已吗?
我的舌根发涩,苦得难以开口。
“你想对我说的就只有这些吗?”
潭林沉默着。
他起身走到桌子旁,又塞了一根烟进嘴里。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是要分手还是怎样都随你,这婚结不结也随你。”
原来在他心里,我的存在微弱得就像一个随时可以打出来的喷嚏。
这八年什么都不算,我也什么都不算。
我的嘴角动了动,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尔后,是轻得如烟灰落地的声音。
“我怀孕了,潭林。”
潭林拿烟的那只手颤抖了。
烟灰竟然真的落在了地上。
可我看着他,心里再也掀不起任何波澜。
“孩子要不要,也由我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