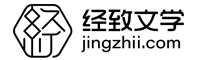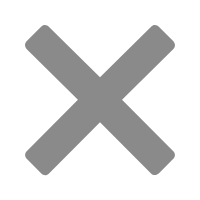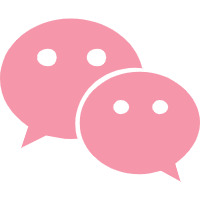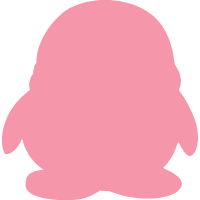-
梨花烬
本书由经致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为抵父债,我签下五年的卖身契,成了商界阎罗俞霄阑的私人藏品。
新婚夜,他掐着我脖颈抵在落地窗上,坚硬的皮带把我的腰硌得生疼。
人前斯文矜贵的俞霄阑,如今眼底却翻涌着欲望:“叫啊,让所有人都听听简大小姐是怎么赎罪的。”
他用力掐着我的腰,不顾我是第一次,把我折腾到了天亮。
次日,父亲落网的新闻却铺天盖地。 我做小伏低,任他玩弄,哀求着他能放过父亲。
他却只是讥讽地开口:“十年前,如果不是你父亲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我的母亲也不会跳楼自杀。”
“他现在是罪有应得,至于你,也该赎罪。”
婚后,他把我圈养起来,不分昼夜地折腾我,让我下不来床。
离五年合约到期还有一个月,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捏着孕检单闯进他的办公室,门外却传来他不屑的语气:“等我玩够了,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肾正好能给阿宁用。”
一个月后,婚约到期。
我服用了一整瓶安眠药,昏沉睡过去,从未感到如此解脱。
他却抛下医院里的白月光,对着我发出绝望地嘶吼:“棠梨, 求你醒醒,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
婚约还有一个月到期,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颤抖着手捏着孕检单去公司找俞霄阑,恰巧听到他耐心的轻哄声:“我娶她,只是为了折磨她。”
嗓音是我很久都没听过的温柔。
“阿宁,你放心吧,明天我就让她签合同,把肾移植给你。”
“俞哥哥,你真好。”
听着办公室里俞霄阑低沉的话语,混着时宁的轻笑声 ,我捏着单子的手指不由泛白。
我知道的,我从来比不上他的青梅,时宁。
掌心在门把手上洇出汗渍,我想起上周我孕吐反应严重,他却不顾我的身体,硬逼我替时宁试药。
每次生病,他都会冷冷地掐着下巴警告我:“别在阿宁面前咳嗽。”
我正打算转身离开,却忽然撞上微阖的门,重心不稳向后倒去。
我尽力小心地护住腹部,却还是疼得忍不住蜷缩。
俞霄阑拽开门时,我正蜷着身子发抖,他皱起眉头,下意识要扶我起来。
指尖刚要触到我手肘,时宁突然轻笑:“俞哥哥,林姐姐真是不小心,这么大人了还会站不稳呢。”
那只手倏然收回,俞霄阑不耐烦地开口:“装够了吗?”
我往后缩时,孕检单从指缝滑落。
他先一步踩住纸角,轻轻拿起印着婴儿雏形的彩超图。
“谁的?”他盯着纸面冷笑。
时宁的鞋轻踩我撑地的手背,语气里尽是惊讶与好奇:“不会是上个月你勾引方董怀上的吧?”
“不”,我紧盯着俞霄阑,不住地摇头:“孩子是你的,我只和你做过。”
俞霄阑冷漠地看着我:“我每次都带套,你说是我的?”
“林棠梨,你真是个不安分的贱货。”
俞霄阑冷笑一声便把孕检单撕得粉碎:“想拿不知哪来的野种骗我?”
碎纸片纷纷扬扬落了一地,他不顾我踉跄着去捡,直接拽住我的手腕往电梯走。
“既然喜欢装,那就去手术室装个够。”
医院走廊惨白得刺目,我被他甩进流产手术室,后背重重磕在冰凉的床上。
我麻木的承受着这一切,却在得知要打掉孩子时陷入巨大的惊慌。
那是我的孩子,那是一条生命啊。
“俞霄阑,孩子真的是你的……”
我挣扎着哭着去抓他的衣角,他却嫌恶地往后推。
“闭嘴,你配怀我的孩子吗?”
麻醉药推进血管的瞬间,我模糊看见他靠在门口抽烟。
烟雾缭绕中,我隐约想起来,和他初识时他曾温柔地抱着我,说以后不会让我吃苦。
可此刻,他对我只剩厌恶与冷漠。
术后我躺在昏暗的病房,浑身像被碾碎,身体感到钻心的寒冷。
门“吱呀”推开,时宁挽着俞霄阑走进来,手里拿着捐肾协议:
“姐姐,谢谢你的肾,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慢慢说着,却往俞霄阑怀里更靠了靠。
俞霄阑沉默地看着我脆弱的样子,眼神复杂。
“俞哥哥,更要谢谢你”,时宁晃着俞霄阑的手臂,轻声撒娇。
俞霄阑转而摸着她的头发,不再看我一眼:“只要你好,什么都值得。”
所以,为了时宁好,就要打掉我的孩子,挖出我的肾吗。
我蜷缩在被子里,任眼泪浸湿枕头。
2
流产后我变得嗜睡,整日萎靡不振,倒在别墅昏暗的卧室里。
最近每晚俞霄阑都会回来。
十点整,玄关处总会准时传来脚步声。
俞霄阑走进来,补品袋子放在床头柜上,发出一声闷响。
“起来吹头发”,他的声音冷硬,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急迫。
我盯着天花板没动,下一秒就被他从床上拽起。
吹风机的热风灼得头皮生疼,我仍一动不动,麻木地承受着。
他似乎有些焦躁,难得的话多了起来:“术后免疫力差,头发不吹干不要睡觉。”
热风吹过后颈,他的指尖突然插入发根:“以前这里有个旋……”
话说到一半,他喉结滚动,忽然哽住了喉咙,猛的加大了吹风机的风力。
他每天都要带来许多补品,如今茶几上的补品堆得像座小山。
撕包装袋时,他总带着股狠劲,像是在泄愤。
我咽不下去,不小心把燕窝粥泼在了地毯上。
他再也装不下去了,猛地掐住我的下巴,冷冷地盯着我。
强硬地把热粥灌进喉咙,烫得我直皱眉。
“喝干净,早点好起来”,他顿了顿:“让阿宁快点换上肾。”
为了她,就把我当畜生吗?
我痛苦地闭上眼,任由汤汁顺着下巴滴在真丝睡裙上,洇出暗黄的印子。
俞霄阑感到没来由的烦闷:“你非要这副死样子?”
望着我脆弱颤抖着的睫毛,苍白的面孔,他眼神倏然变暗。
耳边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俞霄阑上前一步扯开我的衣襟。
月光从窗帘缝漏进来,映得他眼底血丝分明。
他的唇压下来,幽暗的眼神紧紧盯着我,双臂牢牢禁锢住我的身体。
我无法逃脱,只能被迫接受。
我刚流产过,身体还很虚弱,只能低声哀求他不要。
但他却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滚烫的身躯拥紧我,铺天盖地的吻落下。
我用力咬破他的舌尖,血腥味瞬间在唇齿间蔓延,他也丝毫不退。
男人的手缓缓伸入我的睡裙,轻轻拂过我肚子上的疤,引得我忍不住战栗。
他的唇贴在我耳边呢喃:“你在抖……装什么。”
我感到一阵恶心,开始剧烈挣扎。
床头柜的药瓶被扫落,避孕套包装恰好掉了出来,格外刺目。
他撕开时,我哑声开口:“时宁知道你日日与我欢好吗?”
男人动作顿住,继而更凶地撞进来:“林棠梨,这是你欠我的。我给你的一切,你都要感恩戴德的受着。”
一夜荒唐。
我望着天花板,生理性泪水无声滑落。
“孩子真的是你的”,我低声开口,几不可闻。
俞霄阑很久都没说话,开口带着低哑与疲惫:“别再说孩子了,我不想听。”
说罢,他毫不留恋地下床,转身离开。
我轻轻摸着小腹,那里曾经有我和他的孩子。
可现在,被他亲手打掉了,徒留丑陋的疤痕。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我摸向枕头下的安眠药瓶,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具千疮百孔的身体,爱与恨都已烧尽。
死亡,或许是唯一能剪断这乱麻的刀。
俞霄阑,若爱恨都是折磨,那我便先一步逃了这无间地狱……
3
我终日躲在房间里,眼神空洞的盯着日历,等着合约到期那天到来。
还有10天,就要解脱了。
轻轻转动一下干涩的眼球,我竟生出一丝期待。
我死了,俞霄阑会难过吗?
估计不会,他巴不得我死干净好迎娶他的白月光。
深夜,俞霄阑推门闯了进来。
看着我形如枯槁,空洞呆滞的样子,他不耐地点了根烟。
烟圈吐在我面前,引得我止不住的咳嗽。
看着我咳得脸色红润不少,他眉宇间稍微缓和:“明天是阿宁的生日宴,你和我一起去参加。”
他对我说的话,从来都是命令的语气。
我不愿和他再发争执,只背过去不看他。
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我又梦见以前。
俞霄阑是我少年时的悸动,是我青涩的初恋。
他着白衬衣黑裤跪坐在我面前,低声安慰痛经的我。
少年心疼地揉我的肚子,急得险些落泪,傻傻的让我咬他的手。
许诺我嫁给他后,这辈子都不会再让我痛。
梦里的他是那样好,好到我清楚的知道那只是梦。
缓缓醒过来,俞霄阑正趴在我身边。
他似乎睡得很不安,眼角泛起泪光,皱着眉轻声呢喃的我名字。
猛然惊醒,他对上我平静的目光,忽然有些羞恼:
“睡到现在才醒,如果耽误了阿宁的生日宴,你就准备好跪着道歉吧。”
“看你那副要死的样子,真是晦气。”
是啊,我是要死了。
被你逼死的。
时宁的生日宴会上,水晶灯刺得我眼睛生疼,耳膜边觥筹交错的谈笑声我也听不真切。
她身着一袭红裙,笑意盈盈,宛如女王般被众人簇拥。
“阿宁,你可真幸福,听说俞总给你买了一个游艇呢。”
“俞哥哥一直都对我很好”,女人有些娇羞地低下头,转而神色担忧地看着我:“林姐姐不要误会啊,俞哥哥每年都要送我礼物的。”
周围的人仿佛这才发现我的存在,低声议论着我。
“大家不要这么说啊,林姐姐是为了自己的父亲才嫁给俞哥哥的”,时宁大声解释,却引来相反的结果:“他们可是签过契约的,名正言顺的夫妻呢。”
众人一片哗然,我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在戳着我脊梁骨说我不配。
我忽然感到有些闷,准备出去透气。
独自走进电梯,却不想时宁也跟了进来。
门刚合上,她便收起了面上的假笑,故作无意地开口:“林棠梨,我知道那孩子是俞哥哥的。”
“可那又怎么样?可我不过稍作诱导,他就认定你出轨。”
她逼近一步,声音里满是得意:“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打从心底就恨你。”
我知道的。
可是我起那个没能保住的孩子,我心中难以自持地涌上滔天恨意,扬起手便要打她。
就在这时,电梯门突然打开。
俞霄阑正站在门口,眼神冰冷地看着我。
我一滞,手停在半空,干涩地开口:“俞、俞霄阑,你来得正好,她……”
时宁瞬间换上委屈的神情,眼中含泪。
“够了!”俞霄阑打断我,眼神里满是厌恶:“林棠梨,你就这么容不下阿宁?”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她刚才亲口承认了,孩子是你的!是她故意诱导你……”
“你又在提孩子”,俞霄阑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闭了闭眼。
你就是满嘴谎话的贱人。”
“信你?”他冷笑一声。
“你有什么值得信的?”
那一瞬间,我的心彻底凉透,未能说出的话如鲠在喉。
只剩下悲戚的呜咽。
原来在他心里,我从未有过一丝分量。
我颤抖着双手,失魂落魄地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4
回到宴会厅,时宁端来几杯酒,笑意吟吟地看着我:“姐姐,刚才是个误会,来,喝杯酒消消气。”
她身旁的俞霄阑皱着眉,却没有阻止。
我知道,他心底巴不得我出丑。
我被众人推着,一杯杯酒灌进喉咙,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
突然,肚子一阵剧痛,我蜷缩着身子,脸色煞白。
俞霄阑见状,神色微变。
刚要上前,时宁却拉住他,轻声道:“俞哥哥,姐姐也没喝多少呀,怎么会肚子痛?”
他顿住脚步,眼神里的关切瞬间消散,只剩冷漠:“林棠梨,你又在玩什么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