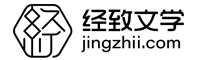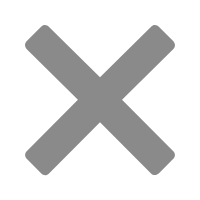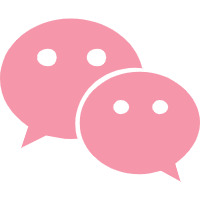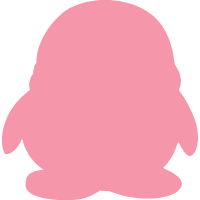-
重生八零,丈夫肩祧三房
本书由经致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1章
上一世,丈夫的双胞胎哥哥突发意外,双双去世,留下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嫂子。
丈夫主动提出要照顾她们。
我忍气吞声,眼睁睁看着丈夫带着两个嫂子进城享福,却把我和儿子丢在乡下吃苦。
他花光积蓄养别人的孩子,而我们的儿子却因为没钱治病,猝死在高考的考场上。
十年后,丈夫衣锦还乡,带着那两个穿金戴银的女人,要和我离婚。
她们嘲笑我儿子是短命鬼,死了活该。
我疯了,跟他们同归于尽。
再睁眼时,我回到了丈夫要带她们进城的那天。
这一次,我笑着接过存折,温柔地说:\\\\\\\"好啊,我理解。\\\\\\\"
……
屋外电闪雷鸣。
我猛地睁开眼睛,耳边嗡嗡作响。
“秀珍和玉兰守寡不容易,我这个当弟弟的不能不管。”
张国栋的声音低沉又笃定,像块石头一样砸在我的心口。
我眨了眨眼,眼前的景象渐渐清晰。
土坯墙上的老黄历,红漆剥落的木柜,还有炕头那盏昏黄的煤油灯。
1985年3月12日,日历上的数字刺得我眼眶发酸。
这不是梦。
我重生了,回到了张国栋决定带两个嫂子进城的那一天。
上一世,他说要照顾守寡的嫂子们,带着她们去了县城,却把我和儿子小军丢在村里。
他每月只寄回十块钱,后来干脆断了联系。
小军为了攒学费,白天上学,晚上去砖窑搬砖,高考那天累得吐了血,暴毙在考场。
十年后,张国栋衣锦还乡,身边跟着穿呢子大衣的曹秀珍和烫了大波浪的赵玉兰。
就连侄女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我的儿子,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桂芬,你发什么愣呢?”
张国栋皱眉看我,手里拿着厂里开的介绍信,“秀珍和玉兰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走。”
我低头,看见小军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他瘦小的身子微微发抖。
“妈,我能去县城上学吗?”他小声问。
张国栋还没说话,曹秀珍就嗤笑一声:“县城学校哪是随便进的?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你一个男娃,在村里读读就行了,将来种地又不靠文凭。”
赵玉兰柔声细语地帮腔:“是啊,小军还小,留在村里多陪陪桂芬妹妹也好。”
我胸口忽然发闷。
上一世,她们就是这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哄得张国栋把好处全给了她们的孩子。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步。
我一把拉住小军的手,抬头看向张国栋:“国栋,我和小军也要去县城。”
屋里瞬间安静。
张国栋脸色变了:“胡闹!厂里只分了两间宿舍,怎么住得下?”
“那就换大点的。”
我盯着他,“你是厂长,这点事都办不到?”
曹秀珍急了,尖着嗓子嚷:“王桂芬!你这不是为难国栋吗?我们孤儿寡母的,好不容易有个落脚的地方,你还来抢?”
赵玉兰眼圈一红,低头抹泪:“桂芬妹妹,你要是嫌弃我们,我们这就回村去……”
张国栋立刻心疼了,转头冲我吼:“你懂什么!我大哥和二哥刚死,秀珍和玉兰日子多难?你就不能体谅点?”
我冷笑:“体谅?行啊,你把存折给我,我和小军在村里自己过。”
“存折?”
张国栋脸色一僵,“你要存折干什么?”
“买米买面,供小军上学。”我死死盯着他,“还是说,你连这点钱都不想给我们娘俩留?”
屋外围观的邻居开始窃窃私语。
张国栋最要面子,被我当众一激,脸上挂不住了。
他咬牙从怀里掏出存折,拍在桌上:“拿去!别让人说我亏待你们!”
曹秀珍尖叫一声扑过来:“不行!那钱是……”
我一把抢过存折,塞进贴身的衣兜里,冲她笑了笑:“秀珍,你放心,我和小军不会白拿这钱。”
张国栋黑着脸摔门出去,曹秀珍和赵玉兰狠狠瞪了我一眼,跟着跑了。
屋里终于只剩我和小军。
“妈……”
小军怯生生地叫我,“我们能去县城了吗?”
我蹲下身,紧紧地抱住他:“能,妈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窗外,暮色沉沉,远处的狗吠声隐约传来。
这一世,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母子。
2
后半夜,院门突然被踹开。
曹秀珍叉着腰站在门口,“王桂芬!你把存折交出来!”
赵玉兰跟在她身后,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桂芬妹妹,那钱是国栋留着给孩子们上学用的”
我冷笑:“小军不是他的孩子?”
“一个男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会种地就行了!”曹秀珍尖着嗓子,“我家大妮可是要考文工团的!”
我懒得理她,转身去收拾包袱。
曹秀珍冲上来扯我胳膊:“贱人!把存折交出来!”
我猛地甩开她:“你再动手试试?”
她踉跄着倒退两步,突然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哭嚎:“没天理啊!小叔子媳妇抢寡妇的钱啊!”
左邻右舍都探出头来看热闹。
张国栋黑着脸从屋里出来,看见这场面,大吼道:“闹什么闹!”
曹秀珍立刻扑过去:“国栋!她要把咱家的钱都卷走!”
张国栋瞪着我:“赶紧把存折拿出来!”
我抱起小军,走到院门口,突然提高嗓门:“张厂长要带着两个寡妇进城,把老婆孩子扔村里饿死,大家评评理啊!”
围观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哎呦,这可不像话.”
“听说那俩寡妇天天往厂长屋里钻.”
“可怜桂芬娘俩.”
张国栋脸上挂不住了,一把拽过我:“你胡说什么!”
我挣开他的手,眼泪说来就来:“存折上是我这些年攒的工资,你要拿去养别人家的孩子?行啊,咱们去公社评理!”
听到公社两个字,张国栋明显慌了。
他今年正要评先进,最怕闹出作风问题。
“你”
他咬牙切齿,“好,存折你拿着。但秀珍和玉兰必须跟我进城!”
曹秀珍不干了:“那钱.”
“闭嘴!”
张国栋吼了一声,又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每月给你十块钱,够你们娘俩花了。”
我抹了把脸,笑了:“行啊。”
等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小军怯生生地扯我衣角:“妈,咱真只要十块钱?”
我摸摸他的头:“傻孩子,存折在妈这儿,他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带着小军去了信用社。
柜台里的姑娘打着哈欠:“大清早的办啥业务?”
“取钱,全取出来。”
姑娘看了眼存折,眼睛瞪得溜圆:“一千二百块?都取?”
“对。”我攥着小军的手,“再开个新户头。”
走出信用社时,太阳刚冒头。
小军紧紧抱着我的布包袱,里面装着崭新的大团结。
“妈,咱现在去哪儿?”
我望了望通往县城的土路:“找你爸去。”
客车摇摇晃晃开了三个钟头。
小军晕车吐了两次,我给他擦了嘴,“忍着点,快到了。”
纺织厂的家属院是几排红砖平房。
我们刚走到第二排,就听见曹秀珍尖细的嗓音:“国栋,这床单咋洗啊?”
我拉着小军站在窗外,看见张国栋正笨手笨脚地搓衣服,曹秀珍和赵玉兰嗑着瓜子坐在旁边。
“嫂子,这被套得用热水烫”张国栋满头大汗。
赵玉兰娇滴滴地说:“国栋,我手都起泡了”
我冷笑一声,抬脚踹开了门。
三人齐刷刷地回头,曹秀珍惊得连嘴里的瓜子皮都忘了吐。
3
赵玉兰最先反应过来,赶紧站起身,脸上堆着笑:“桂芬妹妹来了啊,快坐。”
我没理她,拉着小军径直走到张国栋面前:“怎么,不欢迎?”
张国栋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挤出一句:“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照顾你啊。”我故意提高嗓门,“总不能让你一个大男人,天天给两个寡妇洗床单吧?”
外头几个路过的女工立刻放慢脚步,竖起耳朵听。
曹秀珍腾地站起来,脸上涨得通红:“王桂芬!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我转身打开包袱,拿出新买的搪瓷盆,“国栋,我给你带了新的洗脸盆。”
张国栋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接过盆。
曹秀珍见状,立刻尖着嗓子喊:“哎呀,我那屋的灯泡坏了!”
“我这就去.”张国栋刚要动,我一把拉住他。
“急什么?”我从包袱里又掏出一个纸包,“小军,给你爸看看咱们带什么来了。”
小军怯生生地打开纸包,露出里面油汪汪的腊肉。
张国栋眼睛一亮:“这是.”
“特意从村里张屠户那儿买的。”我故意大声说,“知道你爱吃,花了两块钱呢。”
外头看热闹的女工们发出小声的惊叹。
那时候两块钱能买十斤白面,普通工人半个月才舍得吃一次肉。
赵玉兰盯着腊肉,咽了咽口水:“桂芬妹妹真舍得”
“对自己男人有什么舍不得的?”我笑着看向张国栋,“是吧?”
张国栋脸上有点挂不住,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曹秀珍气得直跺脚:“我那灯泡.”
“自己去总务科领。”张国栋突然不耐烦地摆摆手,“没看见我正跟媳妇说话吗?”
晚上,我在公共厨房做饭。
曹秀珍故意把案板剁得震天响,赵玉兰则在一旁阴阳怪气:“桂芬妹妹,你们娘俩住哪儿啊?宿舍可没空房了。”
我把腊肉切成薄片,头也不抬:“我跟国栋睡里屋,小军睡外间。”
“什么?”曹秀珍差点跳起来,“那我和玉兰”
“你们不是有宿舍吗?”我往锅里倒了点油,“厂里给安排了两间,你们一人一间,多宽敞。”
油锅滋啦一声响,腊肉的香气立刻飘满整个走廊。
几个邻居探头探脑,有个大妈直接走过来:“张厂长家的,做什么这么香?”
“腊肉炒蒜苗。”我笑着递过去一双筷子,“婶子尝尝?”
大妈吃得直咂嘴:“哎呦,这手艺!张厂长好福气啊!”
曹秀珍气得把菜刀一摔,扭头就走。
赵玉兰站在原地,脸色变了几变,阴阳怪气道:“桂芬妹妹,秀珍姐脾气急,你别往心里去。”
我往锅里撒了把盐:“急什么?肉又没长腿,跑不了。”
吃饭时,张国栋破天荒给小军夹了块肉。
曹秀珍在对面桌气得摔了碗。
“怎么了?”张国栋皱眉。
“没事。”曹秀珍咬着牙,“就是觉得,有些人啊,表面装得贤惠,背地里不知道打什么算盘呢。”
我慢条斯理地给小军盛了碗汤:“嫂子,你这话说的,我照顾自家男人还用得着打算盘?”
张国栋的筷子顿在半空。
屋里突然安静得可怕。
“我吃好了。”赵玉兰突然站起来,“国栋,明天厂里发劳保用品,我帮你领了吧?”
“不用。”我抢先说,“以后国栋的事我来操心。”
赵玉兰脸色一僵,曹秀珍直接摔门出去了。
晚上躺下后,张国栋突然问我:“存折里的钱”
“存着呢。”我背对着他,“给小军上学用。”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秀珍她也不容易。”
我没吭声,听着外屋小军均匀的呼吸声。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清晰的影子。
这才第一天,好戏还在后头呢。
4
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外屋有动静。
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看见赵玉兰正往张国栋的搪瓷缸里倒麦乳精。
她穿着件水红色的衬衫,领口敞得老低,一弯腰就能看见里头粉红色的内衣。
“玉兰,起这么早?”我突然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