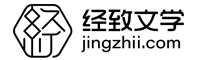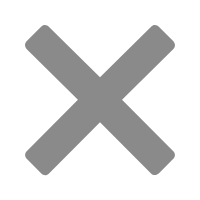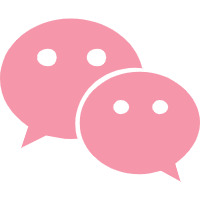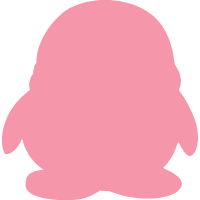-
情深不故
本书由经致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1章
在一起七年,贺绥爱我入骨,却从不许我带助听器。
他在纸上写道,“世界纷扰喧嚣,小宜的世界,只有我就好。”
直到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偷偷攒钱,带上了迷你耳蜗。
却猛然发现贺绥从前的柔情温煦,都不过是包裹在糖衣下的假象。
喂我吃蛋糕时,他眼眸温柔至极,却仗着我听不见,刻薄骂我是个三流货色。
牵着我的手散步时,他掌心暖融,却阴冷的说自己好像在遛一条死狗。
甚至和我在床上抵死缠绵之际,都在对我恶劣的荡妇羞辱。
“沈今宜,你从前有几个男人?怎么稍微玩一下就骚成这样……”
七天后,我留下订婚戒指,离开时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他。
后来听别人说,贺绥家的小聋子跑了,
贺家少爷也疯了……
1
每个抵死缠绵的夜里,贺绥总爱俯身咬我的耳垂,絮絮低语。
但我是个听不见的聋子,无异于对牛弹琴。
为了听清他动情时的爱语,我瞒着他攒钱,偷偷带上助听器。
翻云覆雨之际,贺绥伏在我身上。
眼神温柔如水,轻吐的字句却让我僵在原地。
“沈今宜,你从前有几个男人,是不是人尽可夫?”
黑暗里,我的动作僵住了。
贺绥却恍然不觉,他仍如从前般低垂下面庞,牙齿轻轻厮磨着我的耳廓。
耳畔有热气翻涌,是从前贺绥在床上动情时,向我诉说爱意的前兆。
曾经我恨自己听不见,可好不容易装上耳蜗后,满心期待着。
听到的第一句,却是他玩味刺耳的羞辱。
“嗯?宝贝儿,这么欲求不满,稍微玩一下就骚成这样……”
“存心让我对不起安蕴是不是?妈的,喂不饱的小贱人……”
骚,贱人,人尽可夫。
不会的,贺绥是那样温柔的一个人,他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一定是错觉,一定是……我听错了。
可下一秒,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贺绥摸着我的脸颊,眉目温柔深情。
可随之而来的话语,却嘲弄至极,冷淡鄙夷。
“小聋子,等我玩够了,就把你送给别人玩好不好?”
“呵,你从头到尾,哪里比得上安蕴……”
割裂,太割裂了。
换上助听器,听得见了这件事,贺绥并不知情。
所以现在字字句句,刻薄羞辱的言辞,才是他对我的真心。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如坠冰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眉眼温情,话语绝情。
三金影帝都未尝能有如此演技。
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恐怖?
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不敢想,就在从前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
贺绥究竟仗着我听不见,明里暗里羞辱了我多少句。
最可笑的是,我还以为那是情话,是他爱我入骨的表白。
甚至不惜节衣缩食,买了助听器,想要给他一个无与伦比的惊喜。
却没想到,这个惊喜,先给了我自己。
“呕——”
那晚我受不住,生理性恶心的吐了出来,没有做到最后。
贺绥没有不悦,反而耐心的替我收拾狼藉,小口小口喂我温水。
“今宜,胃病又犯了吗?是我不好,最近没有盯着你吃饭。”
我安静的看着他大半夜忙前忙后,细心温和的模样,一如往昔。
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好好男友啊。
却为何,逐渐模糊了泪眼,唇也咬破?
贺绥,你真的很会演。
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
2
次日清早。
贺绥还躺在身边抱着我,电话响了。
以《春天》为名的小提琴奏鸣曲响起时,我心里猛地一颤。
我知道这是谁的专属铃声,安蕴。
当年就是这一曲独奏,贺绥对安蕴一见钟情,将此作为定情之曲。
“嗯?”
他慵懒的接起电话,声音缱绻含笑,是我很久未曾听过的温柔。
“都说了我肯定会来啊,得捧你的场。”
他还以为我听不见,甚至还明目张胆开了免提。
当女孩清甜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响起时,我生生咬破了嘴皮。
我看着他穿衣离开,还喷了最贵的香水。
起身出门,默默跟在他后面。
那是一处礼堂。
看着门口悬挂着安蕴的巨幅海报时,我苦笑一声。
原来,是她的独奏会。
是啊,除了她,还有谁值得贺绥打扮的花枝招展呢?
买票进场时,独奏会已经开始了。
我坐在台下阴暗的角落,看着安蕴手持小提琴,站在灯光下宛若公主。
曾几何时,我也幻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海外留学、开独奏会、站在闪闪发光的聚光灯下。
但如今,都成奢望泡影,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在距离舞台最近的第一排,我看见了贺绥。
那首《春天》再度响起,他仰头望着安蕴,朝圣般望着自己曾经失去的女神。
眼眸中的温柔忧郁,从未对我流露过半分。
在表演结束后,安蕴拿着话筒感谢了许多人。
“最后一个,我要感谢的,是我亲爱的老同学,贺绥。”
“港城的礼堂档期紧张,如果没有他多日从中周旋,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说着,聚光灯打在了贺绥的身上。
他笑得幸福极了,上台为安蕴送上一束鲜花。
台下有不懂事的观众接连起哄。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我看着安蕴红着脸颊,让大家别闹了,眼睛却很期许的看着贺绥。
当贺绥微微附身,在安蕴脸颊落上一个贴面吻后。
我抬起绵软的胳膊,捂着几乎要碎裂的心脏,快速离开了礼堂。
3
都要走到门口了,我发现左耳的助听器不见了。
这东西贵得很,我得回去找。
礼堂的观众都已经走光了,进门后,我看见贺绥和安蕴站在一起。
璀璨的灯光洒在他们身上,远远望去当真是一对璧人。
贺绥站在一旁,眼角含笑的看着她。
“心情好一些了吗?阿绥。”安蕴轻声问。
“嗯,好多了,不然每天过得和鬼一样,烦死。”
“不快点回去照顾今宜吗?她身边离不开人的。”
听到我的名字,贺绥的脸色冷了几分。
“没事,死不了。”
“你不知道她那副样子,半残不残,软脚虾一样,倒人胃口。”
“这样啊,真是辛苦你了,她个样子,连个猫狗都不如。”
安蕴眨了眨眼,轻轻摸了摸他的脸颊。
贺绥叹了口气,牵住她的手贴着脸。
好似深陷泥沼般的痛苦,唯有她才可以解忧。
我站在原地,如坠冰窟,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
有那么一瞬我希望自己,不是聋了,是瞎了才好。
贺绥,如果我的存在让你既嫌恶,又痛苦。
那又何必彼此折磨?
演着一场本就是假象的幻梦,不累吗。
在两人相拥的瞬间,我抬手打亮礼堂的灯,好戏才刚刚开场。
两人被吓了一跳,齐齐看向我的方向。
“小宜,你怎么……”
看到是我,贺绥愣了愣,眸底划过一丝慌乱。
他下意识将安蕴推开了,向我跑过来。
安蕴站在台上,看了他的背影,咬唇不语。
在他的手如从前那般,向我伸过来时。
我退后一步,向他一字一句的开口:
“沈今宜,你从前有几个男人,是不是人尽可夫?”
“小聋子,等我玩够了,就把你送给别人玩好不好?”
“存心让我对不起安蕴是不是?妈的,喂不饱的小贱人……”
我每说一句,贺绥的脸色就煞白一分。
“你,你能听见了?”
我没有回答,因为一切都不言而喻。
直到他彻底僵在原地,看着我一步步后退。
只留给他最后一句。
“贺绥,我们散了吧。”
4
我并非天生聋子。
是从七年前那场意外开始,听不见的。
我和贺绥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
暗恋贺绥,是全世界唯有我知道的秘密。
大四实习那年,我听说土木专业的贺绥,在工地经常吃不上热乎饭。
便经常带着自制便当,踩着饭点给他送饭。
“哟,小贺,你这小媳妇儿天天送饭,够贤惠啊。”
工地里少见水灵白净的姑娘,因此工友们时常打趣我和他。
“误会了,是我发小。”
“我女朋友娇气的很,这儿多脏,哪舍得让她来。”
可每次,贺绥不是埋头吃饭沉默,就是矢口否认。
我心里发酸,却也无可奈何,偷偷攥紧了衣角。
嗯,贺绥喜欢的从不是我,而是我的舍友安蕴。
她漂亮,聪明,性格好,是音乐系招人喜欢的姑娘。
贺绥对她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
可我是个犟种,我没有办法一夜之间放下对他的喜欢。
所以当工地铁架松动,那块巨沉无比的铁板从天而降的时候。
我几乎毫不犹豫的将他推开。
下一秒,重重的铁板哐当砸在我身上。
在昏迷之前,我只感觉到一阵剧痛和耳鸣……
醒来后,我就彻底听不见了,手臂也变得绵软无力。
医生说我是头部遭到重击,导致了耳蜗与听觉神经受损。
至于手臂,则是伤动了筋骨,不能再抬起来,没有截肢已经是万幸了。
可我是个乐手,是港城最天才的小提琴手。
寂静无声的世界,再也拿不起小提琴的手。
对我来说,无异于梦想夭折,坠入无间地狱。
无异于,成为一个废人。
姐姐来看我,哭得撕心裂肺,但我没听见。
只见她红着眼扇了贺绥一个耳光。
贺绥低着头,脸色苍白的受着我姐的打骂,像块木头,一动不动。
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撞击后的后遗症,让我的耳畔不停环绕着嗡鸣。
在不堪其扰昏过去之前,我似乎看见贺绥抬起头。
他望向了我,说了一句话。
口型是。
“我养她。”
贺绥和安蕴分手那天,他把我拐上了床。
我们的第一次,很痛,痛到我一直在哭。
他抱着我抵在墙上,冰凉的唇将我侵占,舔咬着我残疾的耳朵。
热气温温扑过,贺绥不停的贴在我耳畔说话。
“贺绥…贺绥…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我受不住疼,轻声嘤咛,却又被他粗暴的堵住嘴唇。
“闭嘴。”
月色下,我看清了他的口型。
也感受到了,贺绥在拿我撒气。
但从那第二天开始,他好似脱胎换骨,对我温柔贴心。
姐姐看着我们,也露出些许欣慰的表情。
我以为,自己失去了前途,却获得了真爱,不亏。
自此一步步沉沦在他的温柔乡。
“世界纷扰喧嚣,小安的世界,只有我就好。”
甚至是他在纸上写道,不要我带助听器。
我也乖乖听话照做,安心做一个聋子。
所以如果,如果我没有突发奇想,偷偷带上助听器,永远也不会知道——
喂我吃生日蛋糕时,贺绥的眼眸温柔至极,却仗着我听不见,骂我:
【果然是个三流货色,这种蛋糕狗都不吃】
牵着我的手散步时,他掌心暖融,声音却阴冷刺骨:
【真无趣,感觉自己在溜一条死狗,沈今宜,你怎么还不去死?让我解脱!】
原来我在他心里,是那样的不堪,那样的恶心。
何必呢,贺绥。
我的耳朵是为了救你而聋的。
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强求过你,哪怕一句。
5
散了吧。
贺绥或许从未想到,这三个字会从我口中说出。
毕竟这七年来,我已经被困在他的世界里。
成了一个没有他,就活不了的“废人”。
阴暗的礼堂里,他僵硬的看着我满脸泪痕,心里像是被什么揪紧了。
“小宜,你什么时候能听见的。”